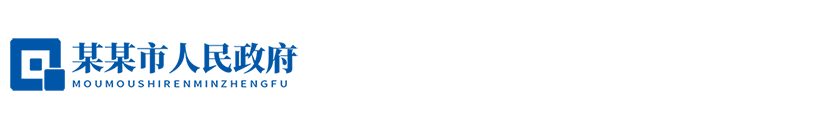习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自人类从动物中走出来那一刻起,就过着一种共同体的生活。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当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回答如下三个问题: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在哪里,与以往各类共同体有什么样的区别?二是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是什么?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以往全球治理方案有何本质区别,有什么样的世界意义?这些问题是基础性的,直接关乎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性、可行性和必要性的看法,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马克思在其相关著作中使用过多种共同体概念,如真正的共同体、现实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共产制共同体、古代共同体、劳动的共同体、原始共同体、部落共同体、天然的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社会共同体、货币共同体等。在马克思那里,这些概念的划分标准和使用语境各不相同,很多不同概念指向同一种共同体形式,并不能表明历史上出现过如此多的共同体形式。但在马克思诸多共同体概念中,一些概念是按照历史维度划分的,这些概念构成了共同体历史发展的时间轴线。
马克思对共同体的历史考察,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在这里,马克思以人和共同体的关系为标准,以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为主线,将共同体划分为依次递进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或天然的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受到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宗法关系的制约,呈现出一种人身依赖关系。第二种是抽象共同体,即货币共同体颠倒而成的资本主义共同体形式,是“纯粹的金钱关系”或物的依赖性关系。第三种是自由人联合体,即阶段的共同体形式。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摆脱了交换价值的抽象统治,摆脱了对物的依赖,实现了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
可见,在马克思诸多共同体概念中,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这三类社会共同体,构成了共同体发展历史坐标中的三大节点。当前中国推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处在由抽象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阶段。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把握唯物史观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防止各种概念的混淆。
在马克思看来,正如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发展到抽象共同体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样,抽象共同体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因此,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定格在抽象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之间虽然正确,但仍然显得过于宏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世界性的历史活动,只有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世界历史”阶段之后才有可能。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点,必然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世界历史”的开辟和形成时期,即商品全球化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世界历史”的快速发展时期,即资本全球化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世界历史”的转型时期,即当今的新经济全球化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第三个阶段的“世界历史”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获得了确证并快速崛起的话,那么,第三个阶段则是现代性后果集中爆发的阶段,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文化危机日益严重化和普遍化,使得过去那种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战争输出的方式难以维系。如果现代性的发展还像之前那样依靠“输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不去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那么,每个国家都会陷入现代性的泥潭中,无法独善其身。
历史已经无数次表明,任何方案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现状和趋势,才能真正得到实施和推广,反之则必然被视为乌托邦式的空想。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的构想不可谓不伟大,但在那个现代性崛起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却不能产生实际作用。当前习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一致赞同和支持,其原因正在于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就在资本全球化转向新经济全球化阶段,就在现代性后果严重化、普遍化并且依靠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的阶段。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理论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探讨,才具有现实意义。
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时代提出的普遍性问题,唤醒了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但是要想真正走出历史困境、解决时代问题,仅有意识和构想是不够的。现阶段是否具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才是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准确把握这一现实基础并促进其发展壮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工作。
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寻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首先要着眼于现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如果当前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转换能够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那么这一构建任务就一定具有可行性。诚然,当今世界的主导生产方式仍处在现代性阶段,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很多方面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发展共同体。在其中,任何一个共同体成员如果得不到发展,必然会退出和反对这一共同体。现代性意义上的发展,是需要很多客观条件的。在传统意义上,全球范围内供发展支配和使用的客观条件是有限的,而发展的需求是无限的,二者之间的冲突势必形成“增长的极限”。发展条件此消彼长的分配格局,必然带来国家间的激烈争夺,进而导致一系列国际战争和冲突。如果不能解决全球发展所需条件的有限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无法真正构建起来。
历史发展不仅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而且在其发展中就已经蕴含着解决问题的答案。这集中体现在当前生产方式新变化与全球发展所需条件有限性矛盾的缓解和克服等方面。当前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原材料需求量和需求形式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发展所需要的空间,逐渐从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向网络虚拟空间倾斜。正如卡斯特所描述的那样,网络空间具有“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在网络中沟通,亦即只要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号(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够整合入新的节点。”网络虚拟空间的出现,使得生产摆脱了地理空间有限性的限制,获得了更加开放的发展潜力。
之所以指认当前全球发展具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除了基于生产方式发展的新变化之外,不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差异性也是重要原因。马克思明确反对人们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认为将“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观点强加给他,会给他带来“过多的侮辱”。历史证明马克思的观点是对的。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同,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站在现有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大大缩短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表明一切后发展国家可以减轻甚至跳过现代性的后果和困境,快速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由此可见,尽管当前不同国家现代化状况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列之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近代以来,为了应对国际战争和冲突,构建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一系列全球治理方案接踵而出,方案的类型不可谓不多,但总体上收获甚微。这不禁令人反思一个重大问题:构建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是否可能?
依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解,构建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战争是伦理发展的必然环节,是保持各民族伦理健康的必要手段,“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应当说,在黑格尔所处的现代性发展阶段,这种理解不仅是正确的,还是相当深刻的。因为黑格尔把握了那个时代主体间、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如前文所述,在各个国家为了实现自我发展而激烈争夺有限的发展条件时,战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和平不过是弱小国家面对大国霸权的无奈选择,或多个大国之间的短期相互制衡。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一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和力量,平衡便必然会被打破,“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仍将继续。
但问题在于,当今世界已经远不是黑格尔所处的那个现代性起步和快速发展的时代,而是处于现代性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今日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严重化和普遍化,并不是靠丛林法则就能根本解决的。对外战争不能确保自身和平,限制他国发展不能确保自我发展。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不共赢就不能单赢,这已经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这时候再抱着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方案不放,显然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了。时代发展呼唤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在这种背景下,习准确把握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首次突破和超越了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方案的单一主体性思维,在主体性基础上强调公共性,开启了全球治理的崭新篇章,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现代性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特点,是所有国家都居于其中的历史境遇。那么,为何唯有中国能够率先提出超越传统现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呢?这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决定的。中国道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从来就不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而始终是一种集体主义或公共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这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从其开启之日起,就与西方经典现代性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的市民社会、原子化的个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中国道路中没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由此可见,习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不仅体现于提出一整套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而且做到了准确把握现代性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成功提出一种超越传统现代性全球治理观和发展观的新方案。其最根本、最重要的世界意义在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拓展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为这种新方案的实施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和鲜活的示范,昭示着这种新方案必将成为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时代之选。
(作者:桑明旭,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郭湛,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誉一级教授)